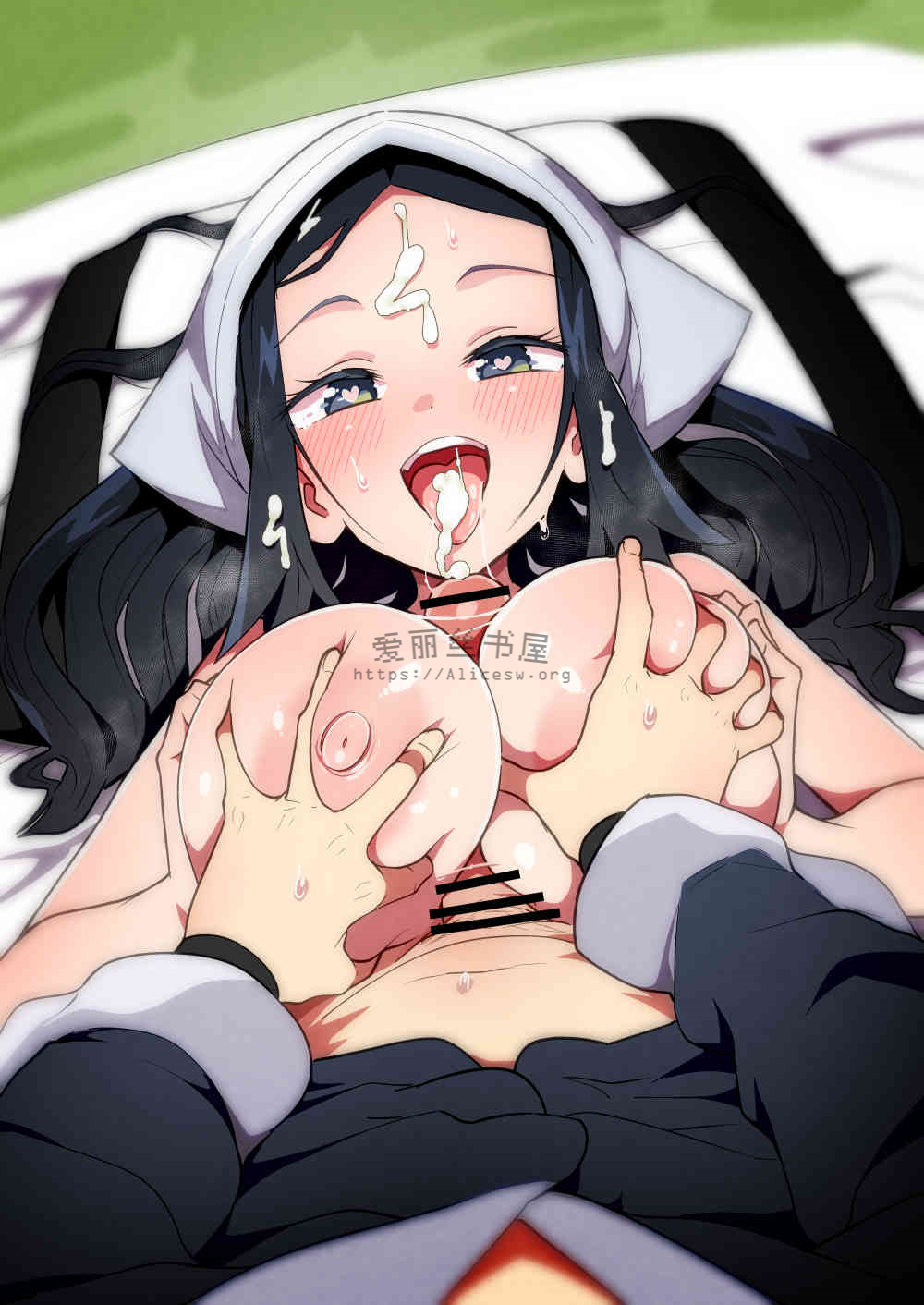第26章 【千粉福利】安全词(上)
一
“安全词?”
这个词儿从医生口中说出来,清清冷冷的,和它的字面儿一样不带一丝欲念。
房间的灯光昏暗中带着些缱倦的暧昧,映亮了医生赤裸身体如雪的肌肤,还有右肩头的斑驳黑色。她洁白的双髀侧蜷在床上,正轻轻抚弄着枕在她膝上的博士栗色的发丝,抚平姌和的余韵。碧潭般的眸子检视着膝上的人儿漾着樱花色的雪白肉体,不知在想着什么。
“嗯。”博士小姐浅笑着,侧过脸庞,面部与医生光洁还带着些微湿气的大腿轻轻磨蹭,气息打在上面,激起温热的涟漪。她侧卧着,伸手抚摸医生颊侧垂到胸前的一缕青丝,捻在手里轻轻把玩。似乎妇妻间云雨初歇后再普通不过的敦伦画面,但她手腕上浅浅的勒痕似乎昭示着一些非比常见。
那是什么?医生想问,却并未出口。她理应无所不知,甚至知晓这个女人就算在被自己要了多少次后依然能想出让自己失态的把戏。比起在病床上艰涩学语的那个活的、彷徨的亡灵,比起那个刚刚穿起白大褂走入实验室、在自己面前表现得无比青涩的巴别塔特殊“新丁”,现在的她多出了一种医生都难摸透的狡黠,似乎那才是她的本性。或许将她推上巴别塔指战员的位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心下里思虑着,手中为博士“顺毛”的动作难免缓慢了几分。博士却得寸进尺,用医生的发梢缠在指尖打了个旋儿,用青色的末梢轻挠医生翘挺的乳头。医生轻轻吸气。“停下。”
“看,凯尔希。”非但没有停下,博士还一边玩弄着挺立的乳首,一边把脸对准了医生两腿间的溪谷,呼出的气息挂在那稀疏的森林上,卖力撩拨。“做的时候,说‘停下’,会被误解为‘想要’。”
酥麻的感觉从敏感处袭来,医生知道,敏感正被博士调戏,自己也正被博士调戏。但她的忍让终究是有限的。轻轻攥住博士的手,几乎没怎么用力便将那恼人的女人制住。医生欺身压了上去,博士笑着阖上眸,任凭医生接吻,接管口腔和一切主动。软舌贴合了许久,间或分开拉出挑逗的银丝,藕断丝连,准备迎接下次。当这个长长的吻结束时,博士已经面色通红,气喘吁吁。感觉到温润的指腹贴上禁地,轻轻分开花瓣的外侧,做好了寝取的准备,博士搂住医生光洁的脊背,在她耳边轻轻吹气:
“而安全词的作用,就是代替‘停下’。”
“是否停下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而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更加了解。”手指的动作开始,身下人的颤抖和喘息近在咫尺。医生轻轻俯下身,却保持着最适中的力度,保持压迫感的同时不至于过多把自己的重量压在她身上。博士轻轻扭动着腰肢,昏黄的灯光照着她动情的面庞,让如丝的媚眼更添上了雨打芭蕉般的情趣。可惜卡兹戴尔贫瘠的大地很少下雨,即便是巴别塔控制的区域,人民也需要深挖水渠。
遇到你之前,我从未想过做这种事;遇到你之后,我做这种事从未想过别人。医生卖力地耕耘着,仿佛今夜就要在卡兹戴尔这片贫瘠已久的土地上挖出一泓崭新的春水,让明年的灌溉更加省力。
其实医生不得不承认,做这种事情时难免有负罪感,远方的人民还在遭受饥寒,对两人间享乐的每一分贪图似乎都是在亵渎殿下和人民的信任。但博士青涩中带着些许妩媚的春声、那属于古人的白纸般纯洁的身体,那樱色的乳首那湿黏甘甜的蜜液由又不得她不加沉醉。尤其那高潮时的紧紧相拥、一声声对她名字的呼唤,那是医生漫长生命间从未感受过的亲热。她对阿米娅是对女儿和学生般的关切和爱护,与殿下之间则是志同道合的崇高友谊。只有这个来自地脉尽绝处的古人,能够跨越一切隔阂,从精神与肉体两方面同她无限接近。
“凯尔希——凯尔希啊!”身下的人儿剧烈地战栗,后背和腰肢上慵懒环绕的四肢猛地收紧,对彼此的一切进以最忠诚的反映。高潮是一种释放,带走浑身的热能。在被情欲炙烤的身体迅速寒冷下来的瞬间,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就近寻找着能够温暖自己的事物,将其作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依靠,唯一的光、热和生命。这是作为群居者的先天之性,也是情爱之事最美妙的所在。博士紧紧拥住医生,肌肤贴合的每一寸似乎都在呢喃,泛起荡漾着的瑰红。
医生心下里警钟微颤。耽于享乐,绝非当下该有的心绪。从温存中缓过神来,医生好看的眉眼倒映着博士幸福而疲倦的笑。她轻轻拥住她,美好到忘我。然而就在凯尔希的手指顺着肋侧滑落,撑起被汗液和爱液黏腻的身体预备再度施为的时候,或许是分离时吹进被褥的一抹凉风,身下人咳嗽了起来,每一声都让医生的心为之一颤。
不仅是贪图的问题。医生从博士身上挪到了身侧,用被子和自己把她包紧。博士立刻把脸埋在医生的肩头,让两人紧紧缠绵,连线条优美的双腿都交错起来难分彼此。医生轻拍着博士脆弱的脊背,心中有些醒悟。她是多么诱人的古人啊,那古老而美好的智慧,那不含任何驳杂的身躯,那会一声又一声呼唤自己的、带着些微调笑的恬淡音色,总是能让自己一次又一次沉迷她的身体,而她又不懂得用她的狡诈拒绝——倒不如说勾引更多些。
怀中的人又有些不安分,栗色的脑袋埋在医生的锁骨前轻轻啃咬。医生抚摸着怀中人的发丝,似乎在默许,但更多是深思中心不在焉的亲昵。或许,主动提出这个要求本就是她希望彼此平等以待的表现?她是否同自己一样,渴求着爱人的身体,又因肩负的责任而不得不警醒自己,隐藏着炽烈的欲念?她是否把这一责任托付给自己,又因自己未能履行而失望呢?
乳尖传来微弱的撕咬感,医生狠狠拍了下博士的脑袋。博士在医生怀里抬起头,做了个鬼脸。
医生说:
“那就听你的,定一个安全词吧。”
“凯尔希最好了~那么,安全词就是……”轻轻用自己的鼻尖蹭了蹭医生的脸,博士对医生附耳了一会儿,医生嗔怪地瞪了博士一眼,象征性地拍了下博士的臀瓣。两人嬉闹了一小会儿,医生的手臂环过博士的颈子,博士如小猫一般缩进医生怀里,就这样沉沉睡去。她的右手同凯尔希蜷在胸前的左手扣在一起,十指错落。
窗外,卡兹戴尔1092年的夏天燥热间带着分许飒凉凄然。
二
1092年冬,夜,巴别塔科研部,核心实验室。
“啊……凯尔希……嗯……”稍稍压抑的声音从遮掩严实的舱门后传出,博士坐在被清空的试验台上,那身遮蔽了外貌的罩袍大半被解下,只剩脱到一半的衣袖从身后限制住双手。医生俯下身,轻轻咬开博士胸前白大褂的衣扣,露出已是思慕了两周的雪白肌肤。虽是如此,她的神情里漾着几分危险,几分严厉。顺手把博士下身的跳蛋又开大了一档,用指尖敲打那起伏的胸口。“知道自己错在哪了么?”
“我……嗯……”尚处自由的双腿被医生轻轻撑开,博士自觉地分开赤裸的下身,接受医生的注视。凉薄的感觉从那里传来,她害怕地微喘——医生不知何时将一柄月光般的手术刀贴在了她的肚腹,凉意从那里渗下肌肤直抵生命的泉口。她本能地颤抖着、蜷缩着试图躲避,每一次同冰冷的接触却又勾引出更多火热。
怎么会这样呢?博士回忆。明明今天是凯旋的时刻,她仅凭一个师和数个从属于巴别塔的佣兵团,从容击退两倍于己之敌的攻击,并围歼特雷西斯手下的主力一个师,使其几乎失去战斗力。那时候参谋们正把电报纸如雪片一般洒上高空,欢呼他们对巴别塔司令长官的爱戴。恰逢那时凯尔希也来司令部接洽伤员的问题,被胜利和因殊烦军务积压了两周的思慕冲昏了的她,当着一众参谋部成员和ACE、斯科特等人的面,喊出了“亲爱的”。
“我记得。”回忆的线被情欲扯断,医生的手顺着被白大褂半掩的乳房向下轻按,蘸着情欲的薄汗按揉,隔着衣服抚摸。带来触电般的快感,却刻意避让开她最敏感的区域。纵横捭阖的棋手在医生面前也不过是任人凌布的媚肉。“我们有约定。”
“不把……我们的……关系……带到工作中……”香汗和花蜜已经在略作磨砂处理的实验桌上洇开了很大一片,她的腰部愈发酥软,几乎坐不稳当。但医生还是不紧不慢按揉着她的躯体,间或用掌尖自下而上,撩起多余的蜜液,探入口中细细品尝。
棋手早就被情欲烧得无法自持,通红的脸儿几欲滴血,却同衣衫整齐、神色淡然的医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医生拾起遥控器,在棋手期待的目光下,跳蛋却突然小了一档。突如其来的落差让她的身躯猛地绷紧,赤裸的下身在实验桌上痛苦地蜷成一团,似乎要用身体从小小的玩具中挤压出足量的快感来。她渴求的眼神看着近在咫尺的医生,但医生突然扭过头,走到相邻的试验台上写起了数据。
“凯尔希……凯尔希!”她难耐地扭动着火烧火燎的身体,爱液顺着桌沿向下流淌。但医生不为所动,那积攒了两周之久的渴求此时成了烧红的铁砧,敲打的是棋手自己的神智。那对修长的腿儿拼命夹紧,局促地扭动着,被大衣束缚的双手也妄想挣脱,最后却不过是在厚实的衣服下越缠越紧,为已经滚烫的身躯浇上名为燥热的油料。
汗水和泪水模糊了视线,几绺散乱的发丝黏在颊侧。她在桌子上侧过身,不顾廉耻地摩擦着双股。近乎沸腾的快感却就是无法冲破阈值。每当她感到将要成功的时候,身下的跳蛋似乎都被刻意调得更小。凭她狼狈不堪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今天早上她还意气风发,指挥着这片土地上足足几万人的武装力量。
“凯尔希……我知错了……求你……”看着凯尔希再度走到面前,博士苦苦哀求道。但医生只是把一管针剂打进她的静脉。“既然出任巴别塔的司令长官,你就该知道,这个约定的重要性。”
“我们的关系曝光,一来会削减内部对于军队指挥层和科研部门协同的合理性的信任,二来会给我们彼此带来不必要的把柄。”透明的药液被推入体内,博士轻轻咬住下唇,闭上眼睛承受着自血管发散延伸的欲望。“这是拷问用的试剂,会加快你的神经元传导速度,本来用于刺激痛觉。”她的声音清冷,脸上没有表情。“这是……我作为巴别塔高层,对你对组织造成的潜在危害的惩罚。”
她将博士抱下桌子,离开桌面时被浸湿了一半的罩袍终于完全脱落,如同脱下一个笨重的壳儿。博士被医生放在椅子上,双手本能地颤抖着朝下身探去,却又被医生轻而易举地擒住,如变戏法一般亮出一条棉绳,不顾博士微弱的抗议,医生将那早已脱力的身躯连同半脱落的白大褂牢牢反绑在了椅子上。“现在我要去处理一组实验数据,对讲机我会放在桌子上。”
她看着博士,碧色的眸子是严肃的,带些戏谑的快意。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从那里对我说就好。”
“凯尔希,求求你,求求你……”博士依然想做最后的告饶,但舱门已经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她徒劳地磨蹭着双腿,再一次陷入到情欲的海洋中。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验数据要处理,为了今晚,她连续加了两天的班儿。凯尔希只是在门外搬过一把椅子坐下,静静地看着书。看完了一个小节,就拿起手边的遥控器随意调大或者调小一个档儿。耳麦里传来的喘息声和呻吟声也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只是思绪牵萦着,书中的东西入了眼,却从心头滑冰一般消却了。
“我?真的可以么?虽然我也曾是……凯尔希,我真的曾是个军官么?”
我为什么要肯定地回答她?凭冬眠舱上残破的军官照,还有那被时间锈蚀到只剩轮廓的军队徽记?
“凯尔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家的味道,太熟悉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她的天赋究竟从何而来?这如蒙尘的璀璨突然显世的天赋,又会给巴别塔,给这片大地带来什么?
“或许只是累了,或许是新奇感作祟——放心,凯尔希,放心,我很好,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我为你而战,也为殿下而战。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我却一直只是个不足道的研究助理……我也理应起到作用,这不仅是回报你和殿下,也是为了这个饱受苦难和风雨的萨卡兹民族。”
“人民万岁,凯尔希。”
是该庆幸,还是该羞愧?
回过神来时,耳麦里的声音不知何时停了,夜晚静得可怕,只有墙壁上的钟表在滴答作响。她察觉到自己的下身也有些湿润,不由轻轻叹了口气,起身打开舱门。
博士的双手依然被紧缚在椅背后,那装满了诡计的榛首低垂着。凯尔希察觉到不对,快走了几步,才看到棋手的美目轻阖,睡脸在实验室肃净的白色灯光下显现出几分安然,已经昏了过去。地板上有莫名的水渍,遥控跳蛋不知怎么被她弄出了体外,静静躺在椅边,仍在执拗地嗡鸣。
她抱起博士,触手才发觉那赤裸的娇躯有些发烫。博士本来就忙于指挥连续两个星期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儿,还在作战结束后开专门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找自己。医生看着她面前始终正常运作的对讲机,碧色的眸子黯然了几分。
凯尔希轻柔地抚开棋手小姐脸上的发丝,吻了她的唇角。有那么一刻,她有些希望棋手小姐突然睁开眼,用独属于她的俏皮语气嘲弄她的愧疚神情。但理想总和现实相去很远。棋手并未醒来。她柔柔弱弱地依偎在医生怀里,身体随呼吸而规律地起伏着。
研究所内已经没人了,医生用衣服把棋手包好,如同运送一个大号布娃娃一般把她搬到车的后座,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后来,每当博士问医生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总少不得被医生呵斥一番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狠狠地在床上“收拾”。然而在博士酣然入眠时,医生总是睡不着。她把博士如同大号抱枕一般拥在怀里,一边暖着她的身体,一边试图揣测她的心。真诚和虚伪在这个传奇的棋手身上共存,就算医生可以无限次攫取她的肉体、温存她的心扉,却也依然看不透棋局中那些深沉存在的忧思,以及寄托于那深思的布局。在漫长的生命中她也曾输过无数次的博弈,而如若回头看去,同这个人的博弈她从来胜算无几。
她依稀记得科研部的下属们在那件事后的谈话。
“要我说,博士都和部长勾搭上了,那以后战场上和巴别塔总部守备医疗队配属的事情直接向博士请示算了——啊啊啊部长我错了!”
三
“朋戊,巴别塔乃至卡兹戴尔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当然是特雷西娅殿下。”身板挺拔的龙族男性随着身着黑色风衣的无征种女性走在林荫道上。在卡兹戴尔难见这样的林荫,为了军校的环境,殿下特地派人多挖了一条水渠。
博士沉默。李伯明知道这是对他回答的默杀。“可是,恩师,您明明在课上说……”
“如果你想听到和萨卡兹学员们同样的东西,自然无须来这里同我散步,第一食堂的酒吧和音乐室在等着你,朋戊。”博士停下脚步,她比这个炎国军人低一头,但当她仰视那双乌黑的瞳孔时,后者错过了目光。“这里没有监控,内务部的人在跟着那几个佣兵团里提拔出来的学员。说说你的看法,朋戊。”
“伯明恳请导师教诲。”黑色的眸子中并非顺从,而是内敛。博士凝视了他半晌,恍然大悟。她轻轻叹气,自顾说道:“因为你是炎国人,朋戊。你所侍奉的君王稳固到无须更多的忠诚,因为这忠诚已化作大炎广袤疆土的身体发肤。所以这句话,朋戊,我要说给你听。”
圣人云,因材施教。离乱于漫漫长夜的萨卡兹民族需要的是照破迷惘的明灯,而在长明膏烛的照耀下趱行了两千余年的大炎需要的是颂鸣万民的钟声。当时,博士并不知晓李伯明身后的那些深重,她只如姑且一试,埋下一枚并未承载多少希望的花种。
“朋戊,记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平凡地结束了一天的授课,博士乘车离开了皇家军校,离开了这片除了司令部外她在卡兹戴尔的大地上停留时间第二长的土地。一出学校的院墙瞬时便是两个世界。她在远离窝棚区的地方停了车,如普通归家前的人妇般买了些兽肉。由于缺乏砍价的精力,还被菜贩平白多收了不少钱。这个季节蔬菜是罕有的,块茎植物是唯一的选择。
“我回来啦。”推开住所的门,她想起同医生的约定——不如说是死皮赖脸求医生终于得来的结果,面红心跳是免不了的。可医生并不在家,或许还在加班吧?她熟练地把苦芋去皮,同带着骨的兽肉炖在一起,主食则是头天剩下的面饼,放在风干箱里避免腐坏。作为皇女的臂膀、组织第三号人物,她完全有权吃到舰内温室新鲜的蔬菜、和阿米娅一同住在临时王庭里随时聆听王的教导。但她做出了和医生同样的选择,将王庭的位置留给立功的萨卡兹们。
香气溢满了房间,她也换上了居家的服饰,栗色的长发随意拢在脑后扎了个低马尾,宽松的晨衣于入1903年初春的料峭来说有些不耐,但她依然感觉到了燥热。她放任炖锅咕嘟着馥郁的味道,在卧室内翻找着。棉绳——医生坚持用之前用干净的沸水煮一下,跳蛋——在医用的无菌密封袋里,源石电池对于两人来说都不具危险。眼罩——一块干净的黑布。没有束缚嘴巴的东西,医生不喜欢断绝她交流的权力。游戏是双向的,她们也是双向的。
想象着这些东西今晚用在自己身上的样子,棋手小姐的下身有些隐隐的黏滑感。她郑重其事地把这些东西整齐摆在床头柜上。想象着医生把自己扑倒在床上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儿,她不由自主地把双手背到了身后,仿佛已经被医生娴熟地反绑。医生会挑起她的下巴,一边责怪她不该急急忙忙把她叫回家只为了这种事,一边在她得意的笑声中吻住她的唇。她闭上眼睛,晨衣下的双腿轻轻厮磨着,试图模拟那完全被掌控的感觉。万物都是互补的,战场上的控局者只有在被完全掌控的时候才能重拾作为人的自知,不至于迷茫,不至于错误。
可是,什么是错误?
“凯尔希……凯尔希……”
并未用手指解决,就如医生平日里欺负自己的手段那样,撩拨得欲火焚身却偏偏剥夺双手的动作。博士侧倚在床上,修长的腿儿不断磨蹭着,亵裤的布片早就被浸透,更多黏腻顺着双腿温和地流淌,被睡衣的布料抹匀成两髀间急速冰冷的火热。她剧烈喘息着,手指紧紧抓住床单,好似想象中同医生十指相靠。终于再也难以忍耐,她把手伸入宽松的衣服下,从里面褪下了湿透的布料,仅仅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令小股的热泉再度润湿了指尖。
“凯尔希……唔……”
“我想你,凯尔希,我好想你……啊……”另一只手轻轻揉搓着乳房,用掌心拢住乳首温柔地按揉,模仿医生最惯用的手法。博士一次次唤着心上人的名字,但与火热相对的唯有空寂。
所幸并未沉沦得太久,她喘息稍定,起身去关掉炖锅的火苗。两腿间的潮湿感仍未发解,似乎刚才的宽慰并未起到太大的效果。她把炖菜端上桌,摆好两人的餐具,开始望向窗外的夜空,想要从中描摹医生的身影。
滴滴滴——
然而棋手也并不总能预料一切。预料中的门铃没有响起,反而终端的提示音捷足先登,打破了氤氲的气息。博士好看的眉眼拧了起来,许久才扶额轻叹一声,连饭菜都来不及去收拾,披上衣柜里的罩袍,戴上面具便出了门。
对于巴别塔来说,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夜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