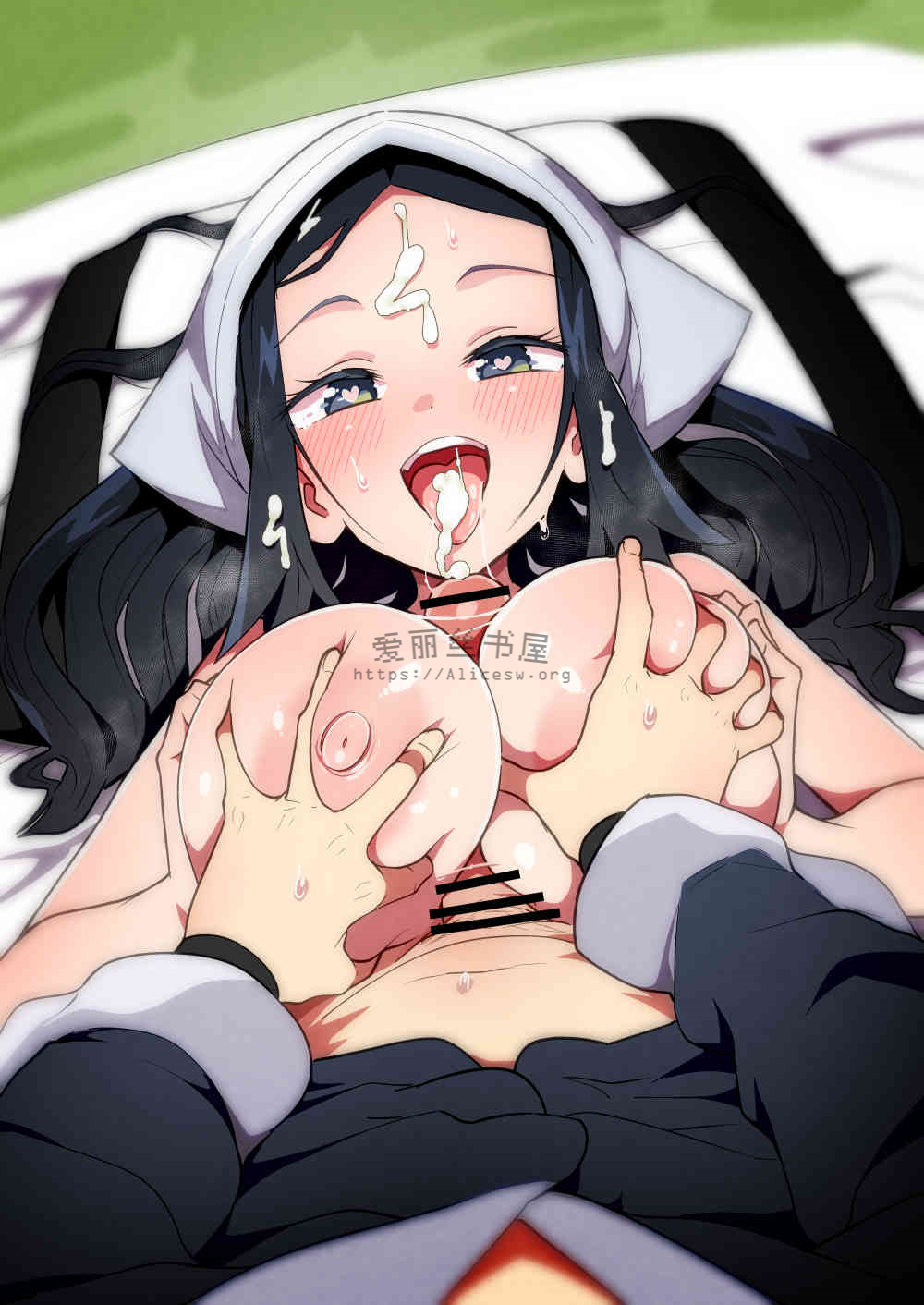第21章 提琴
“那,博士,我们就走啦。”
穿着军装的索尼娅走到我的面前,似乎终于假装出一种听起来随便的口气。那稍稍有些躲闪的神色让我隐隐好笑,却又笑不出来。
“一路顺风。”我对她轻轻颔首。天生就是领袖的她本就不该以我为目标,她有属于她的更宽广的未来。“我希望在将来,你能站到我所需要仰视的地方。”
“理所应当。”她挺直了腰板,摆出一张臭脸。“我这就带他们去找你说的那个什么伊里奇,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能让你这混蛋把我们让出去?”
挥手作别,我看到她走到远些的地方去,背过身用袄袖胡乱擦着脸。今晚,她们将离开这座大地中聊以荫蔽的母舰,走向残酷而未知的未来。我看着交通舱里逐渐稀少的人影,想着那五个稚气未脱的身影踏上吃人的大地,走入无尽风沙中,我突然有种巨大的空虚感,仿佛体内一直支撑着的某一根梁椽倏然折断。周围的夜色狠狠朝我压了下来。一瞬的脱力,我撑着墙面,喘息良久。
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生命把绚丽的愿景和光彩的明天向未来前去了~
我们的愿望插上翅膀徜徉城市的雨声叮当~
宇宙间最真挚的美丽献礼为我们所品尝~
那是小提琴么?
我抬起头,循着声音回到音乐室,方才摩肩接踵的舞台已人影零零。娇小的卡特斯漫步在台上,小提琴奏响,音声里仿佛也晕染着离愁丝缕。我静静地在台下落座,看着她。阿米娅仿佛并未意料到我的到来,她黑丝包裹的纤腿迈着如殿下般规整优雅的步子,闭上眼睛沉浸在音声当中。但我察觉到,她将身体转向了我这边。无言,是最温柔的关怀。
音声撩拨着我的思绪。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巴别塔冰凉肃杀的金属舱壁搭建的实验室中么?曾几何时,我能回忆的以前似乎都被那枚碧叶占满,其他人的身影都是那样的模糊。想想也是——冬眠舱中新醒来的带着惶恐的死魂灵,又怎有余裕光顾其他人的伤痛?我只愿意回忆我的归属,我的挚爱。
那时候我刚刚获准离开房间,逡巡于舱室间狭小的自由中,将笔记本上凯尔希一字一句教给我的现代语默诵。冬眠舱带来的深重死气仍未洗清,那时候的我只要走得久一点,就必须哪怕就地坐下来,喘息上好久好久。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自苏醒后第一次听到了小提琴。
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生命把绚丽的愿景和光彩的明天向未来前去了~
发颤的乐符组成弦,展现着艺术的脆弱与美好。那是记忆深处的声音,是在每一场夜雨中不散的温柔的风。一开始还以为是医生的雅好,直到有一次,在每日例行的见面后她行将离开,琴声飘摇进来,凝滞了她的脚步。
“那是...谁?”悠扬的音色间,我生涩地发音。
“另一位病人。”医生侧耳倾听,碧玉般的面容泛起了丝丝柔情。
那是我第一次谈起我们之外的第三人。即便语言尚未谙熟,音乐却能超脱一切文字的隔阂。我猜测着那优美琴声后的灵魂,从娟秀清丽的女子到英俊羞赧的少年。一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的琴声就该是什么样的。我猜测演奏者或许不曾有太深沉的阅历,因为那音声比山巅新淌的泉水更清冽;我也猜测演奏者曾阅读过许多,因为那音声比古籍里星罗的字迹更幽深。直到我学会了语言,恢复了似乎与生俱来的技巧,愿意并能够为我心所属的医生帮手的时候,我才看到病床上娇小的女孩,难以置信,她的床头摆着一架小提琴。
“她...”我结结巴巴地,连说带着比划:“叫...什么...名字...”
“阿米娅。”医生答道。
“博士?博士?”柔美的轻唤把我唤回罗德岛处于尼古拉塔楼阴影下的现实。音乐室的灯不知何时熄了,只剩门外廊道素白的照明。她站在我面前,蓝宝石一样的瞳孔在黑暗中更显深邃,我知道,那里面满溢着这个年纪所不该承受的绝深感情。
“博士很难过。”她说道,陈述的口气杜绝我辩驳的心思。
“是啊,别离是车裂活的灵魂,把碎片扔到大地的某一处,可能很久都找不回来。”我歪过头去,并非为了躲避视线带来的流露,只是不想令她看到我的眼泪。
“博士,您说过,自治团的明天要她们自己取得,我们不该干预。您...对,您还说过,离开的人并没有离开,他们的精神同罗德岛同在!”小小的手突然抓住我的胳臂,带着少女未艾的气力轻轻摇晃。她努力寻找着我曾说过的词儿句儿,安慰着言不由衷的虚伪的我。
是该庆幸,还是该羞愧?我攥住她娇小的手,即便是握过剑的手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粗糙或冰凉,柔软却同戒指和质化的坚硬一起无声的恸哭。坚硬侵占柔软是大地的本质。我如此,凯尔希如此,阿米娅也如此。黑暗中,坐着的我稍稍比站着的她矮一点,她颤巍巍地伸出手,如我每一次抚摸她一样,抚摸我的头。
这大胆的行为令我怔了一下,身体不自主地前倾,等我恢复神智时,我发觉自己不知何时把脸埋在了她的怀里,少女淡淡的体香熏染着神智,就算看不到,我也能想象出女孩那红透了的面庞。但她依然抚摸着我的发丝,声音不带一丝的战栗。
“博士,一直都是您来保护大家,如果累了,医生又不在的话...就来找我吧。”
真的可以么?我察觉到自己的泪水早已晕染开了女孩胸前的布料,洇湿包被下的美好。椅子在轻响中被推开,我起身将温软的身体拥入怀中,感受着十四岁少女酥柔的身躯,任凭兔耳打着脸颊。如果是医生的话。我想。我此时肯定已经扑到她怀里嚎啕大哭,然后被她半是嫌弃半是安慰地按在墙上深吻了吧。
思念至此,唇边居然真的感受到了温软。生涩而熟悉,她正踮起脚尖,学着医生的样子努力地碰着我的唇。青涩的香味带着微苦,和医生是那样相似,但却不具有猞猁的侵略性,嘴唇擦碰,多出了兔儿的生涩和跳脱。
我揽住她的身体,显得过大的外套立刻塌陷下去,显露出女孩实际上的娇小可人。我的手在女孩白色毛衣和黑色裤袜下已经开始凸显的曲线上游走,听着兔儿稚嫩的喘息。奇异的是该有的负罪感却并未泛起涟漪,我们是一体的,罗德岛的大脑、精神和脊梁本来就是一体,再多的亲密似乎也理所应当。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并不贴切的旧日的词儿在我脑海中响起。昔日只有我腰部高的她此时终于能踮起脚同我接吻,但仅止步于嘴唇擦碰的她却不知晓这几乎是勾引。我的舌头不自觉地伸进了她的嘴儿。医生常说我的舌头很滑,滑到她经常捉不住,对此我反笑她那生着肉刺的舌儿和她本人一样古板。而如今,当我轻易地捉住阿米娅不知道躲闪的香软,才知道医生所说确有道理所在。我自然而然地抱起她,她环住我的颈子,以公主抱的方式继续接吻。我想起在核心城战役的末尾,我也曾像这样将她抱下战场。
踏着夜色将她抱回她自己的房间,就像凯尔希曾经这样把我抱回安寝。她刚一被放在床上就迫不及待地加力揽住我的肩背,似乎生怕我撒手。我低下头,同她再度接吻。兔的渴求和猞猁那从容猎手的渴求不同,兔是急迫的种族,生存的危机带来短暂生命更多的繁覆。她主动牵引着我的手探入白色毛衣的下摆,避过白嫩肌肤上黑色的裂绺。
“博士...要我脱掉么?”她看着我,情绪仿佛凝成了某种实体,在少女的闺房中聚集成一片粉红。
“不用,这样的阿米娅也很可爱。”
“哎嘿...博士...”女孩露出了满足的笑,她主动引导着我的手,游走着解开款式尚属稚嫩的胸衣,带着女孩的温香从衣衫的下摆滑脱开去。明明同我还有医生同样平坦的胸脯,在她娇小的身姿上却尤其娇嫩可人,甚至能感到那胸腔里小小的生命欢快地搏动,宛若永恒。
“博士...”喘息声一点点撩拨着我的心思,试图掩盖长久以来的伤痛。她蹬掉小皮鞋,配合我褪下她短裙的动作。我侧过头去,轻舔女孩娇艳欲滴的耳垂,换来阵阵长吟。“博士...”
“还叫博士么?”在黑丝上轻轻抚摸,滑细的触感轻奏着靡靡的歌。怪不得这物事那样受企鹅物流的疯丫头们推崇。随着手指滑向裆部,小兔子的两股微微夹紧,那里已有些浸润了。
“呜...欺负人...”她的眼神里也溢出了水光,少女的身体隔着被掀开了半边的毛衣透漏着暗香。“妈...妈妈...啊!”
我半是好气半是好笑,食指隔着裤袜的布料轻轻一勾,便能贴切感受到少女下身的痉挛,一小股热流隔着黑丝喷在指尖,煞是美妙。“都说了,凯尔希才是妈妈。”
“可是亚叶都叫您师母。”难得调皮一回的小兔子在我身下偷偷笑着。很明显,在但凡知晓我和凯尔希关系的人面前,我总是难保全自己的脸面。手指报复性地进取,尽情领略着时隔许久而未能见证长成的少女身姿。回想起第一次看到她病床上的身体时,她还是那样贫瘠而娇小,未开发的土地却被黑色的裂绺争先。我的心隐隐痛着,手指不由自主地抚摸着黑玉般点缀的质化,带起女孩轻微的哼叫。
“Doc...Mum”她用她襁褓中的语言唤着我,主动磨蹭着双股,尝试着褪下那块紧要的布料。我懊恼自己的分神,欺身而上,用更激烈的吻安慰着兔儿那渴奶婴孩般的渴求。她轻轻吮吸着我的唇,似乎要把唾液当做乳汁,汲取安慰,汲取生命。
“Mum...给我...”我无言地将她尚欠丰腴的双腿向上打开,剥下黑丝时发觉爱液已经在大腿洇湿了一大片,连床单都晕开了深色的斑块。兔性本淫,这一回我可深有察觉。手指轻轻拨开细嫩的包皮,抚摸着她珍藏了十四年的软肉。
“...Mum。”起初是受刺激的轻呼,随即却是动情的迎合。她的手不自觉地搓揉着娇小的胸脯,凭经验我一眼便看出女孩平日里自慰的手法。顺遂着她的动作,我扣住她的手,用她自己的掌心给予她自己。吻上那波光粼粼的蓝色明眸。她长长的耳朵耷拉下来,全身心地接纳我。这是抚慰,亦是传授。仅仅这小小的刺激就让她进入了一个小高潮,我转动着我的手指,看着银丝在指尖如琴弦般拉长,消逝。
“阿米娅,我的孩子,我的珍宝...”前欺身体,将她的上半身彻底推倒在床上,我小心地将她的双腿折叠向上张开。她羞红的面容没有躲避,流着涎水的小嘴还在轻轻回应着我的呼唤。我把脸贴近她耷下的长耳,轻吹着绒毛,感受薄薄皮肤下血管的温度。“让妈妈看看,好孩子有什么进步,好么?”
“嗯...”她如蚊鸣般回应着,双手却很坚定地主动拨开小阴唇,把花核无保留地呈现给我。我用湿淋淋的手指再度触碰那里,比每一次身体检查都更加细致。女孩的花壁被轻轻搅动,淫靡的水声不时随着离体的水渍显现。我低下头吻住泉口,口手并用,另一只手则轻轻按摩着女孩粉红的菊穴。
“啊...博...妈妈,女儿,阿米娅...要去了...”逐渐激烈的动作很快就让女孩无法自持,我感到口中的花蕊似乎也在搏动,颤抖着将甘美的热泉送入我的口中。女孩包裹在黑丝中的腿儿被我架在肩头,无助地颤抖着,研磨着我的肩颈,别样的滑腻触感。
“去吧,阿米娅,我会看着你的。”看着她,就像从前所期盼的那样看着她长大。可怜我缺席了女孩成长中重要的三年,但我们间的亲情并未因别离疏远。罗德岛的大脑曾为旧的灵魂效忠,也愿意为新的灵魂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我们间永恒不变的约定。
热泉淋漓在我的面孔,温热的味道虽然是第一次品味,却如早已熟悉般感到亲切。我放下那对黑丝包裹的纤腿,递身把脸凑近她,鼻尖相碰。她喘息了一会儿,伸出粉红色的小舌,主动舔舐着我脸上属于她的液体...
脸上的湿黏让我口干舌燥,不由一口气吻了下去,向她交换她自己的味道,把她口中的津液又尽数收回......
暴风雨过后,宁静重新归复。她有些不耐地在凌乱不堪的衣装下挣扎着,我便索性将她剥光,让她足够放松地躺在床上。
“博士...”她似乎也恢复了些微的理智,似乎想起了刚才的疯狂,赤裸着被我护在怀里的女孩脸上重新摆起了那小大人的矜持。“我的表现...和凯尔希医生比起来怎么样?”
“很棒,阿米娅,很棒。”我搂着她,有些忍俊不禁。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啊,怎么能吃医生的醋呢。“阿米娅看过我和凯尔希做么?”
“没...没有。”小兔子羞赧地扭过头去。“只是...听到过。”我故作生气地刮了下她的鼻尖,她反过来搂住我的腰肢,无言地撒着娇。如平常母女一般在床上嬉闹了一番,似乎是不敢过分用力,她很轻易被我压在了身下。保持着这个暧昧的姿势,女孩残存着些许潮红的躯体又颤抖起来。“博士,能不能...”
“叫妈妈。”我笑着吻了下她的眼睑。啊,错了错了,不是应该让她叫爸爸么?
“妈妈。”不等我纠正,她主动把脑袋埋在了我的肩窝里,呼出的热气轻轻打着我的锁骨。“妈妈,想要。”
其实,就算她不说,我大致也忍不住了吧?轻轻抚摸女孩再度潮湿的腿儿,拦截那成股淌下的花蜜,我想到。
......
“啊...妈妈...妈妈!”
“阿米娅...我的好女儿...啊...”
花瓣间的研磨总是让美好绽放的最优选。我学着凯尔希往日的样子,牵住小兔子的手,感受着她的花蜜淌入我体内的感觉。如果她真的是我生的该有多少?如同乱伦,把花液喷入曾孕育了自己的温床。但并没有。我拧动着腰肢,最大程度给予女孩刺激,令她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她在我身下颤抖着,战栗着,蓝色的眸子里溢满了幸福。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动作,我们的股间在每一次磨蹭时都拉出淫靡的丝线,像是杂乱的弦。我和她用身体共同演奏者禁断的音乐,袅袅不绝,直入夜深......
温柔缱眷的月光在黑夜中洒下银白色的轻纱。简单清理了欢爱的痕迹,为睡熟的她穿好睡衣,我坐在女孩窗前的黑暗中。月光好似带着古远批判意味的女神,刻意映亮洁白床单上戴满蓝色戒指的手,无意地用美丽强调着残缺。
以前,以后。
如果凯尔希是我的以前,那她便是我的以后,罗德岛的以后。以后——未知的黑暗深渊。魔族的王啊,你将往何处?
我看着那床褥下娇弱的女孩,突然感觉如临深渊的痛楚。我记得,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她娇小的身躯持着长剑,英气逼人地屹立在烈焰当中。经历了那场大战的萨卡兹干员们说,那一夜,他们梦见百万雄兵。
我静静坐在床边,女孩闺房的气息轻扰着鼻尖。握住那娇小病态的手,女孩袖口下的黑色纹路半掩在睡衣袖下,比任何一位传说中的英雄都平静地接纳着悲剧。
“我见源石,遍布大地,我见魔王,头戴皇冠,将万千生灵,熬做回忆...”
暗合图谶。想起七千万年前祖国的史书中曾提过的词儿,我感到撕裂般的疼痛。这疼痛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殿下。我手上的鲜血无法濯清,因为我和殿下一样都必须负责对人民。世界人民必须自己向地平上可能的曙色去追寻,而不应该寄希望于某个王——倘若历史被强加于个人,悲剧将成为唯一可能的结局。殿下天人般的面容在脑海中浮现又消逝于血污。我和殿下一同谋杀了殿下自己。人民是杀不死的,但个人能。
眼泪不争气地落下。黑暗中,我看到一道红光,它凌厉如闪电,它温柔地逡巡。似乎犹豫了良久,它一口气贯穿罩袍和白大褂,击穿了我的胸膛。我感到沉淀在生命深处的情绪被漩涡激起,化作心灵深潭的一片晕染开的污浊。悲戚从眼眶溢出,我哭得浑身战栗,不能自己。恍然间感觉一个纤弱的身体搂了上来,长长的耳朵扑簌在脸上,有些微痒。
博士。我听见怀里的女孩抽泣。博士。
脑海中的种种情绪逐渐消散一空,只剩下那个裹着白大褂的我和身着病服的娇小的她。小提琴的声音悠扬而宁静,似乎要屏蔽开一切黑暗,让时间永恒。
怀里的温暖和柔软抬起了头,我看到那双宝蓝色的美丽瞳孔。兔儿的眼睛凝着浓浓的担忧,她不愿读我的心,却能体察我的痛。她的担忧却令我更加痛楚——如果她真的看到了我膺中的曾经,会不会像医生那样因我的罪恶而变得冰冷?
“博士!”我听到她在唤我的名字,我反过来拥住她。任凭第二道红光从她体内射出,将我的胸腔和灵魂一并贯透......
我睁开眼,却发现自己依然紧攥着她的手。消耗了太多体力的女孩还在安睡。在我们相握的手上,另一只柔荑覆在我的手背,我循着它向上,看到黑暗中玉藕一般的纤细臂膀,看到了医生隐隐愠怒的神情。
“啊。”我轻声道。“你回来啦。”
她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高高扬起。我地闭上眼,轻咬着舌尖生怕惨叫声吵醒了孩子。但最后只是感觉冰凉覆盖住面容。她轻轻摸着我的脸,像是擦拭其上的泪痕。
“这孩子,还是那么依赖你。”凯尔希看着床上的阿米娅,眸色幽深,看不出是嗔是叹。
“她和你就没这么亲。”我半开玩笑道。
“孩子都更亲母亲。”她反唇相讥,把我的手从女孩的手上拿开,攥在她的掌心里。阿米娅在睡梦中轻哼一声。
“那个...我们先出去吧,别吵到她。”哪怕心里溢满了不妙,我也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想挣脱,却被死死攥住,怎么也不肯放松。
“她的身体条件不适宜在担负我离舰两天的半数工作后又剧烈活动。”医生翻了翻女孩的眼皮,神色愠怒。很显然,我能找到的任何借口在凯尔希面前都是那样不堪一击。她粗暴地拥我入怀,深吻下去。
我感受到猞猁的舌头粗暴地探入口腔,凯尔希似乎打定主意把我嘴巴里的每一寸都扫过,把我口中所有属于阿米娅的味道都据为己有,比搜查物证的警官还要执着。背后一凉,触碰坚硬,我知道自己正被她按在墙上压吻。如我今夜一开始所幻想的那般。一切都会迟到,但一切都不爽约。
“至少...别在这里...”轻声向她求饶,我看到猞猁那双猎手的眸子里的狠厉,不由有些脊背发凉,也不知是舱壁的凉意渗入,还是自身怕得冰冷。和阿米娅做我已经消耗了不少的体力,如果再被猞猁狠狠要一晚上的话...
但一切终究不遂我的意愿,只要她愿意,我永远逃不出她的掌心。随着她的手探入我的睡衣,我只觉浑身的力气就像被那只略微冰冷的纤手抽走,脑海中再也存不来半分的反抗念头。刚刚齐整过来的衣衫被剥落,月光洒在彼此苍白的肌肤上,冰冷而坚定。
“轻...轻点。”被推倒在熟睡的阿米娅身边,感受着肌肤裸露于空气的凉意,我略微慌张地唤她,却被医生掐住了乳尖,呻吟几乎要破口而出。“是谁连孩子的身子都要馋?”碧眸盯视着我,我感觉脸上发烫,想扭过头去,却被她托着下巴强行对视。“不想吵醒她,就自己忍住吧。”
“唔...”还想轻声争辩,却不得不捂住嘴巴避免释放出快感。医生的手指轻易便探了进来,几乎毫无犹豫地直取花心,熟练拨开细微的皱褶,指腹轻而易举触碰那团若有若无的软肉。我感觉下身酥麻的电流顺着骨盆蔓延,嘴巴已把虎口咬得泛红。凯尔希对我阵地的每一寸都熟悉到可怕,这场防御战注定是无谓的抵抗。
玉指在体内轻轻转动,变幻着一片淫靡。另一只手轻巧地顺着腹部按压,令内壁更加紧致地研磨着侵入。胸部虽然未被侵犯,但她碧色的眸子在黑暗中也明着,有如视奸一般从我挺立的乳尖上扫过。
“真是淫荡的身体...”她轻声责骂,落到耳中却仿佛连听觉都在被抚慰。天啊,天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该防守的地方还有更多。她把面埋在我的胸前,气息顺着浅浅的沟壑蔓延,一只手轻轻按在我的颅侧,撩起一绺栗色的发丝,当着我的面含在口中品尝。由于她趴伏在我身上,我甚至能看到绿大褂被重力下牵时那未着遮掩的一对美好。这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令我神情恍惚,依然被她时快时慢抽送着的花径一阵剧烈的抽搐。我努力把头扭向一边。阿米娅的睡颜再度映入眼帘。我是罪人,受到的惩罚却不能被受害者看见,这好比命运的惯性,更是棋局的必然。
沾染了我自己温度的素手将我捂住自己嘴巴的手强硬地挪开,侵占最后的防线,医生的脸逐渐凑近,脖颈上传来毛刺照顾的刺痒感。不等我有所回应,冰凉的玉牙便印上了颈子薄薄的皮肤。我感受到猞猁的利齿已同我颈动脉的每一次呼吸趋同,那是一种绝对的被掌控感。医生知晓我内心的渴望,一切欢好在她面前都无所遁隐。
我闭上眼,咬住自己的舌尖,医生的呼气声和下体的水声在耳边响起。与其说是最后的抵抗,不如说是被猞猁咬住了喉咙的猎物在争取仅剩的尊严。但这也终于要以破碎告终——下身被抽送的速度愈发的快,每一击都恰到好处刺在敏感。
“唔...凯尔希...不要——啊...”然而就在我彻底投降的前一秒,嘴巴猛然被封住。这让慌张的我难以自持,险些咬破了医生的唇。下身就像放了闸的水坝,无声的接吻间,我顺着身体听见潺潺的春水顺着青葱外流,打在暧昧的床单。我浑身的力气随之而去,当她的嘴巴挪开,我不顾唇角的银线断裂,忙扭过头,阿米娅的睡眼依旧,女孩的唇角在黑暗中微翘着,似乎做了好梦。长长地松了口气,我这才注意到医生正把湿透的食中二指从我体内拔出,把上面的拉丝挂在我的乳尖。
长久的无语,我伸出手,医生安静地将我抱起,随手拽起罩袍把我包得像个襁褓里的婴儿,她抱着我,就如我来时抱着阿米娅一样,静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或许吧。在身体离开潮湿床铺的一瞬,我听到了女孩被子里轻微的嘤咛。无奈地一笑,我揽住医生的颈,任凭她把我朝她的房间带去。
明天,或许干员们又没机会向他们的博士问早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