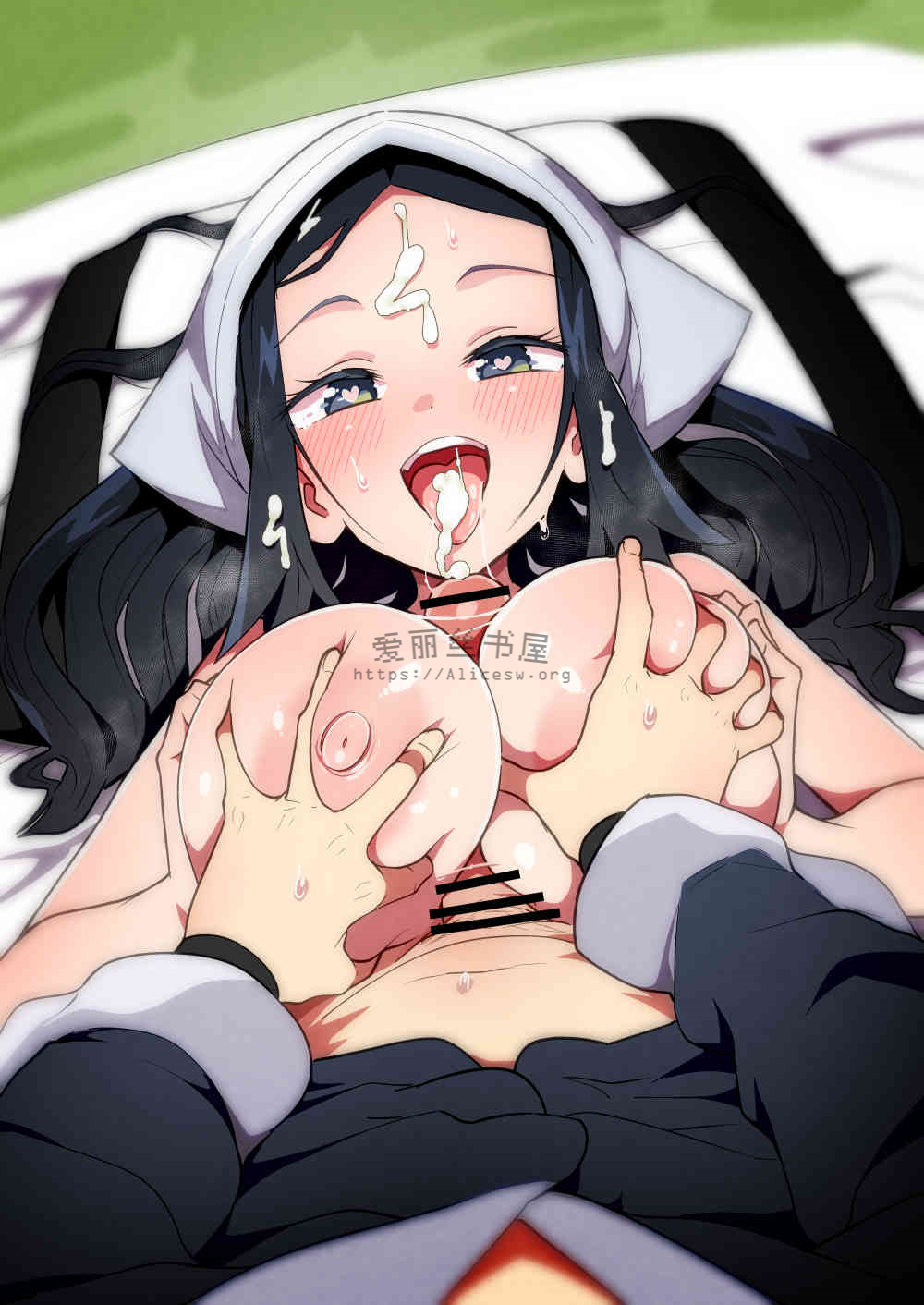第52章 棋手小姐驭雁【煌x灰喉】
出北庭道首府常七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处草原叫做灵原。风吹草低的苍苍茫茫间,马蹄踏过葳蕤的草木,给予无限远景以铁血的气和骨。两队骑士正在草原中列开阵势,好似对彼此虎视眈眈的敌人。但若再做远眺,便可看到高丘处停驻的第三支马队,簇拥着一架古老拙劲的军鼓。军鼓旁骑在马上那高大挺拔的龙族军人面色严肃,按在吴钩弯剑上的手向前一指。随着军鼓咚咚,两队人马飞快地启动,向彼此的方向挺近。
“那边红衣的是大炎边军‘骧骑’。”灰喉听见煌在自己耳边不住兴奋地絮叨。“太厉害了,我小时候经常在报上看见他们!”
灰喉眯眼看去。两队骑士的装备差异很大。右侧一方是红衣红甲的炎军骑士。就像煌所说的那样,在大炎,连三尺孩儿都能知晓他们的马上英姿,如数家珍般道出他们的恢弘事迹。他们的长矛长弓是大炎几百年以来的铮铮干城,他们人具马装,近乎传说中的战神般刀枪不入。他们金铁盔上璀璨的红缨在传说中驱散鞑虏,在史书上留下一次又一次的“苍鹰扑雀”。
“那左边的是什么?”虽然满心不愿意在担任护卫时多嘴,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灰喉悄悄问道。
“左边的……我也不太清楚。”这话立刻招来燕子的一个白眼。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左侧一方军士与先前的全然不同。他们的装束虽然精良,但比起红衣的重甲骑士轻便到不可思议。一身黛青色的紧身军装,配以高筒马靴。战术马甲紧紧裹在身上,让他们的身形比起对方整整小了一圈。军帽饰以碧玉,脖颈上却悬挂着乌黑的防毒面具。轻便的弯月战刀挥舞起来如一道道银色光电。他们的速度远比重甲骑士快,几乎顷刻之间已经逼近敌方不过百米之处。
“放箭!”
红衣骑士的队列中一排排长弓拽响,利箭抛投九天而后雷霆而落。青衣骑士呼啦一声散布开来,如一朵青色乌云云雾般围拢。这些轻骑纵使速度惊人,也不敌神箭的强劲,到底有不少人马中箭,连人带马重重倒地。但剩余的人仍如闪电突掣,不等第二波箭雨来临便濒临搏杀之处。
“散骑冲锋!让开正面,包抄左右!”为首的青年龙族军人一挥弯月战刀,怒吼之下,轻骑兵避开了正面竖起的森森长矛,青色乌云化作流水从侧路冲击着红色磐石。黛青色的身影冲击极快,生生在重骑列阵下撕开了几道裂隙。
“分散列阵!三骑骓!”红甲骑士之中军官一声令下,红衣炎军一哄而散,化整为零,以三骑为一组,三个三骑又是一个小组,每组之间互相照应,每位冲击入阵的青衣骑士都要面对三个以上的红衣骑士,却又无法立刻将之击落马下。纵使集中十余骑冲锋,也无法破得三骑成阵,反而在阵阵呼应长枪交错之间,自身落于下风。纵使有个别骑士勇猛非常,也砍不倒几名红甲骑兵。渐渐的,青色潮水被一柄柄的红色利剑切割开来,互相离散,难以形成有效的冲击。
“千机弩!”青衣骑兵似乎也识得三骑骓的厉害,甫一交手纷纷后撤以保持距离,从马上掏出轻便的自动弩机。红衣骑兵虽也有远攻,但近身厮杀后长弓便不便利频繁使用。但青衣骑兵的自动弩操作简便、火力迅猛,近身攒射之下,纵使红衣骑兵衣甲厚实,也不住有士兵落马。青衣骑兵立刻拔出马弯刀席卷,一时间大有撕开红衣骑兵阵型之势。
“北庭雁骑,雁行云驰,飞步电蹄,骁比龙骧,真新军之楷模哉!”李伯明身边穿着黛青色军装的女性军官笑着低声道。“朋戊,论练兵之法,你却可以做我导师了。”
“恩师说笑了。雁骑由族弟教训,不过半年。能够熟稔新式军法已属不易,当不起恩师夸赞。”李伯明含蓄笑道,但黑眸子中骄傲自不必多提。
“差不多了,还记得我告诉你的事么?”博士面色一正。
“恩师放心,事情我已交代族弟,他有分寸。”
“李毕恭是将才,但太年轻了,该多加锤炼。”
“伯明谨记恩师教诲。”
此时场中大战局势渐渐异变。红衣炎军虽然前军被冲乱,但后军在前军掩护下迅速重新结阵。速度之快,即便青衣骑士已经飞速分出一股袭其后队,也被其射来的长箭击退。重新结阵后的重甲骑兵气势大不相同,彼此之间如山岳连绵,最前一排团牌并举,封住了雨点般的自动弩攒射。后队爆喝一声,长矛鱼贯投掷而出。大量青衣骑士中矛倒地,冲击之势一瞬溃散。随后红衣骑士重新结为三骑骓,此时青衣骑士已经萧疏零落,无力再行冲锋。看起来胜负已定,无须再战了。
“今日演练,骧骑胜!”行军司马高声道。
“好!今日回营兄弟们有肥羊炖!锅盔管够!”
“才不吃什么砖头一样的野战军粮!哈哈!”
“就是!小包小裹,娘皮一样,没劲!”
红衣炎军呼拥哄笑着去了,猎猎劲草中只有黛青色的骑兵,纷纷扶起伤兵,从地上爬了起来。为首的年轻龙族军官跑到李伯明面前敬了个军礼,两眼微微有点发红。“节度使,这群狗娘养的——”
“无碍。”李伯明云淡风轻摇摇头。“作训半年,能与大炎边军百年积淀之精锐相骈,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饭要一口口吃。”
“是。”李毕恭眼中仍有不甘,但依旧去号令雁骑收队。草原之上风吹草低,远处牧民口中的大黑丘仿佛睡在天陲的巨人,硕大无朋身体显露黑黝光泽。
“恩师,您觉得,这北庭雁骑,比您手里的菁英干员如何?”李伯明突然问。
“雁骑为新军翘楚,光是数量,便同整个罗德岛能拿出来的武装力量等同。我却是拿什么来比?”博士笑道。
“不,恩师,久闻罗德岛菁英干员多奇人异士,皆可独当一面。伯明想要看看,雁骑若单打独斗,能否同此类人士相骈。”李伯明说话间,眼神不经意地从博士身后仍穿着罗德岛墨蓝色作战装束的煌和灰喉身上转了一圈。
“这……”博士略微迟疑,煌却突然高声道:“博士,我接了!离乡这么多年,好久没见识过军中的勇士了,也好练练手,松松筋骨!”
“蠢猫,你搞什么——”灰喉嗔道,煌满不在乎地在马背上抻了个懒腰,笑嘻嘻的样子就像是没看见。
“好!煌小姐爽快。”李伯明趁势把事定下,博士便也不好推诿了。便让行军司马传李毕恭过来。看到煌笑嘻嘻地打马迎出去,灰喉心里像是堵了什么一样不自主。但看到博士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也不好发作。这个蠢猫,怎么到哪里第一时间都想着惹祸;比武也就比了,何苦非要同那领兵的官长比!想要赌气挪开视线,却又做不到不管不顾。
“放心,干员灰喉。雁骑乃至炎军,不逞个人勇武。军中总长乃是能够调度之人,却未必强过一个普通劲士。”博士看出灰喉的窘迫,好心提点了一句。此时雁骑整队已毕。李毕恭随着行军司马与煌,三骑骈行回到军鼓前。行军司马在马上对李伯明一礼:“敢问节度使,若要李校尉与这位煌小姐比武,是步战?是马战?”
“入乡随俗,马战吧!”煌抢在李伯明前面道。
李毕恭斜扫一眼煌挎在腰间一人高的链锯,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我看免了,煌小姐愿意讨教,只怕施展起来军马受不住。还是主随客便,步战吧。”
“毕恭,煌小姐是罗德岛的菁英突击干员,若是步战,谁向谁讨教可说不定了。”李伯明打趣道。
李毕恭一下涨红了脸。“毕恭来北庭前,也是步卒,族兄怎么尽涨他人志气?”言毕翻身下马,跟随煌走入阵中。北庭雁骑一字列开马阵,势同长蛇。在广袤草原之间,围拢成一个青色的方阵。李毕恭立于阵中,黛青色的军装与漆黑的马甲浑同一体,肃杀凌然,竟同煌在龙门见过的黑蓑影卫有几分相似。四周雁骑齐声高呼,为其长官助力。
“喂,怎么都一边倒啊?博士!灰喉!”煌不满地抗议,风把她的声音传到博士和灰喉的耳畔。
“煌,加油!”博士高声,同时轻轻推了下灰喉的后背。灰喉心思不宁,一个收摄不住,居然连同战马朝前窜了两步。她顿时大窘,轻叱一声,策马回到博士身后。
煌远远看到灰喉的样子,不由会心一笑,从随身匣内取出链锯,只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甩掉身上的防辐射罩袍,只留罗德岛墨蓝色的作战服,外罩防弹衣,拉下目镜。理了理在脑后扎成一束的马尾。
“北庭军骑兵01团上校团长,检校*上府振威校尉,李毕恭!”李毕恭拱手,赳赳有声。弯月战刀铮然出窍竖持额前,高筒马靴一划摆开架势。
“罗德岛菁英突击干员,煌。”煌有样学样对着李毕恭一拱手。草原之上风声萧瑟,草叶吹过兵刃,一瞬被裁成两截飞散飘扬。
“杀!”李毕恭赫然先攻,军靴踏劲草行步如疾风,竟似一道青黑色的闪电转瞬杀到煌面前不过五步距离。煌面色一肃,未及预热的大锯高举向下来了个力劈华山。满以为李毕恭若不行躲避,必定被这势大力沉的一锯撞个头破血流。谁料那口弯月战刀不闪不让,对着大锯逆行而上。四下里雁骑齐声一叹!
“铮!”
煌心中惊呼,那看似细长的弯月战刀论分量居然全不似看起来那般轻,居然硬撼重锯之下既没有被挑飞又没有豁口崩刃。不及惊叹,李毕恭已经变招,战刀在锯上一磕斜刺里冲杀过来。煌奋起浑身力气抬锯扫荡挡住刀锋,但李毕恭之刀势又不仅于此。见一击不中,居然引身向上在电锯手柄上一踏借力,整个人从煌头顶空翻而过,战刀一横,煌的发辫顿时爆散飘扬,缕缕青丝顺着狂风卷入苍茫草场。
“彩!”周围雁骑齐喝,就连煌都不忍喊了一声好。抬手拆下一截绑带,重新绑好马尾,一甩大锯重新摆开架势。
“请赐教!”李毕恭重新摆开架势,战刀竖立额前,黑眸子中倨傲溢于言表。
“恩师,您看,哪一方能胜?”李伯明问。博士笑笑:“雁骑人具马装,皆是下足成本,这一身别看轻便,却暗藏玄机。若煌不知晓这其中的奥妙,这一场她必败无疑。”
“恩师此言差矣。”李伯明正色。“战场之胜败,在于人。毕恭虽自幼习武,又做了统领,但终究没能亲历沙场遍览世事。怎能与煌小姐多年出生入死之经验相骈?”博士笑而不语。
也正如博士所说的那样,煌现在倍感压力。李毕恭的战刀不知用的什么合金,坚韧质密不输链锯,偏偏在此人乃至这些雁骑手中又能轮转如飞。如果仅凭技巧相对,竟然全无取胜把握。她扫一眼身后不远处正目不转睛看着自己的灰喉,毫不犹豫地使出了杀手锏。点点血滴从大猫的毛孔中渗入空气,连串的爆裂带着热浪四散开来。乘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她的身体连同合金链锯一跃而起,朝着李毕恭狠狠砸去。
李毕恭见热浪来时,一刀扫劈自身腾空而起。两人兵刃倏忽相撞相离,李毕恭趁势抬脚,嵌着钢板的高筒马靴直踹煌的心窝。煌一手撑锯用肘抵挡,大锯在热能的催动下高速旋转,终于将李毕恭的战刀磕开。但李毕恭整个人已扑到煌的近身,完全不给链锯施展余地。煌一手控锯力气分散,近身与李毕恭揉打两回合,已是落于下风。冷不防被李毕恭一个双拳贯耳,回身迫肩摔连人带锯掀翻在地。李毕恭向前一步双手举战刀要劈煌的脑袋,煌弃锯抬腿踹中李毕恭后心。李毕恭借力前滚翻稳住身形,藏刀于背反身拦腰一刀,劈在横置的电锯上。他一抬头,早已将煌刚刚起身匆忙拦截露出的破绽看在眼里。正欲抽刀斜劈,异变突生。
“沸腾……”
点点血珠在煌的全力催动下争先恐后渗出毛孔,随着她的动作竟纷纷朝李毕恭砸来,铁锈味直冲鼻腔,热浪滚沸四散涤荡。漫天血点映在李毕恭瞳仁中,竟是十二分的骇人。
“感染者的血?”心中倏忽转过这么个念头,李毕恭持刀的手一松,居然伸手去抓脖子上挂着的防毒面具。心神一分,煌裹挟着澎湃的热能反手一锯横扫而出。
“爆裂!”
然而就在那些即将连串爆炸的血滴将李毕恭整个人笼罩时,他黛青色军帽上的玉佩青光一闪,一道清凉的光晕当头照下,瞬间将凝化了煌全部源石技艺的沸腾爆裂消融一空。煌大吃一惊,没有源石技艺加持的链锯倏忽停转,杀伤力几乎骤减为零。但李毕恭同样只顾规避,不仅错过这一绝好的反击机会,身上黛青色军装到底还是被链锯刮了一下,豁开一道血口,所幸侵彻不深。
-----------------------
“你这蠢猫,长点脑子啊!”
劳碌了整整一天,甫一回到扎营的地方,立马呈大字型扑倒在那柔软舒适的牧榻上,抛开所有思绪美美地睡一觉——煌是这么幻想的。
然而现实是,刚一进帐篷,立马被火急火燎的燕子按着坐在床上——拿着红药水和酒精棉强迫她脱下上衫。大猫的身材因久经锻炼而健美遒劲,分明却又不过分舒展的肌肉线条透漏着精干的美感。但其上的伤疤同样多到吓人,今日新留下的青紫斑驳着分布在光裸的后背和上肢。灰喉隐隐想起大抵是两三年前看到过的博士的身体,她们并肩行了这么久,伤疤也亦步亦趋了这么久。
“嘿哈~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这点小伤又不碍事。”好像棉签戳到了痒点,大猫的身体以常人很难做到的幅度扭动了一下,没有束带约束的乳球摇晃着晃花了燕子的眼睛。“再说,今天你女人不是赢了吗,有什么好——哎呦!”
手从煌手臂内侧的软肉上挪开,掠过右臂尤为可怖的一道伤疤。那场战斗中如果医疗支援慢上五分钟,煌日后恐怕就得永远以义肢度日了。灰喉又从后面锤了煌一拳。“臭美。”
“我还是赢了嘛。”煌耍赖道。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李毕恭不管是格斗还是刀术都让煌棘手无比,再加上那可以瞬间将源石技艺变得软弱无力的特殊装备,足以令煌没有任何胜机。倘若真如博士所说,李毕恭的实力并不比任何一名雁骑突出,那便意味着随便一名雁骑就能对抗一名菁英干员。而这样的雁骑足有一团之数,与罗德岛本部能拿出的全部武装力量数量等同。想到这里,灰喉满心都是不可思议。
罗德岛如果单独直面国家机器,必定被彻底碾碎不留痕迹。但博士就是带领着这样的罗德岛,经历了整个乌萨斯,而现在又要参与大炎的棋局。灰喉静静从后面抱住了煌。夜晚很静,能听见风吹过草原,打在帐篷上的沙沙声。不得不说,两人居然在此时还能拥有彼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灰喉将她的想法讲给煌听了,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奇迹?”她任凭燕子抱着她的后背,自顾啪的一声,将落在身上的一只蚊子打扁,接着从一旁的行李里取出了源石驱虫器。“菁英干员们一路走过来,没有谁觉得我们在创造奇迹。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接着往下走,从卡兹戴尔出来是如此,去乌萨斯也是如此。”
灰喉不做声,煌继续说:“离开乌萨斯的时候那支军队里和我们并肩作战过的朋友来看过我。他们问我,罗德岛干嘛不留下?明明新政权赞同感染者的权利,也急需药品。”
“那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燕子问。
“我说,我们的根不在这里。”煌干笑了一声。“绝大多数菁英干员是感染者。我们本来都该烂在地里,无人知道。不过在罗德岛这面旗帜下,我们可以在死前做点事情,或者轰轰烈烈地去死,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燕子又不做声了。煌嘻嘻一笑,突然抓住从后面抱住自己的燕子的手臂。一个熟练的反擒拿。灰喉连惊呼声都来不及发出,身体已经被煌紧紧压制在下面。
“而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大概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燕子吧~”
“咕……呜”
等不及再说什么,嘴巴已经被滚烫的唇舌给封住。煌身上的味儿很杂,未发解的淡淡汗香,红药水和酒精的味道,血的锈味,还有草原里新鲜草叶的清甜气味。在高体温的加持下,这些味道经常久久萦绕在灰喉身边。即便黎博利是善于目视的种族,也不能忽视这其中晕染的信息在心间久久盘桓。
“想得那么多,可是会老得快哦。”好不容易从煌的嘴巴里解脱,灰喉刚刚抬起头,脸儿立刻被两团脂肪压住。她发出模糊的抗议声,手无力地推搡着煌的肩头。很难想象煌平日里带着这样的负重跑上跑下,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煌的身体稍稍下挪,解放灰喉闷得通红的脸儿,她们的胸口隔着一层薄薄的衣衫磨蹭着。
“你这……蠢猫……”无力的抗议,灰喉的身体在煌身下象征性地挣扎着,却并没有阻止煌用嘴巴咬开她的衣扣。对于黎博利来说,灰喉的尺寸可谓不小,甫一弹出,带出的是并不比煌逊色多少的暧昧。她轻声训斥着作乱的煌,任凭带着倒刺的猫舍扫过自己胸前的软肉,一直向下,打湿皮肤,濡湿羽毛——猫吃鸟的必然过程。
准备的衣服有限,可不能撕破了。煌强压着心头的欲念,耐着性子脱下灰喉的衣服。有些地方勒得尤其紧,用力一扯就带起一圈红痕。灰喉痛得闷哼了一声,似乎在责怪煌的粗暴。但煌确认的是,灰喉已经做好了准备——脱下装的时候,那里已经是湿的了。
带着猫刺的猫舌顺着灰喉的身体一路吃下,在玉女峰的丘壑间舔上唾液,落下水渍。数千万年前,黎博利的祖先是无须哺乳的种族。但即便在那时,她们的胸脯同样被捕食者视为最鲜美的一块肉。煌如婴孩般吸吮着灰喉的两点嫣红,用自己的胸脯按摩、挑逗着灰喉的小腹。
“嗯……”灰喉的斥责声终于不再有出口的机会,转而被一声接一声的呻吟挤占。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煌的发丝,与其是想阻止,不如说是按着她的脑袋求她不要离开。煌微微一笑,对着灰喉同样有形的腹部呼了一口热气,感受她身体的颤抖,异常美妙。
手指和舌头顺着微微显出线条的腹肌一路按压,略过脐间,从那里到达腹下。煌一点点褪下灰喉潮热的亵裤,显露出长着平坦灰色草坪的耻丘。距离第一次结合已经过去如此之久,不用太多的迟疑和交流,她轻轻含住灰喉的花核,舌头朝里面探索。
“啊!”轻声的惊呼,带着毛刺的舌头直接刺激阴道壁,像是戳破熟透的果实,从里面涌出一股鲜甜的花汁。然而被浇了一脸的煌没有半点嫌弃,而是愈发火热地去亲吻、舔舐。煌把灰喉的双腿托起,稍稍一用劲,黎博利那轻盈的下半身就被她整个抬了起来,灰喉不得不用双手撑在头顶,任凭煌傲人的胸部顶着自己的后腰,以跪坐的姿势尽情舔舐爱抚着下体。唾液与爱液混杂着从耻丘淌落,顺着腹部向乳沟滑去。
“灰喉,你这样好可爱。”从灰喉的大腿间抬起头,煌能看到爱人绯红的面色和不由自主抓紧了枕套的手儿。弩手的手劲自然不会太小,也为煌所喜欢的这种大胆的体位提供了可能。煌一边热情的舔舐着,一边把手伸向自己的下身,就用灰喉刻意压低了的呻吟当配菜,自顾自地娱乐起来。
“呜……蠢猫……你……啊……”灰喉本能地扭动着下身,腰肢危险地倾斜了一下。但煌仅用一只手抓得也很紧,甚至还有余裕在雪白的大腿上揩油。
“灰喉……啾……”虽然没有什么东西直接进入,但煌的舌头在此时并不比她的电锯逊色。虽然灰喉同样受过菁英干员的训练,但依然很难与她相比。带着软刺的舌儿来回在阴道上剐蹭,时不时轻轻吮吸,将更多液体带到表层。灰喉感觉小腹里的火热持续积攒着,终于在一阵又一阵过电般的抽搐下顺着下体一泄如注。
“呼……哈。”
火热过后的冷静总令人思维格外明晰。夜晚的凉意点点洒落彼此赤裸的肌肤。夜深了。
煌喜欢把灰喉紧紧拥在怀里,大猫火炉一样的身体是所有温暖的来源。灰喉也喜欢在每次的高潮后与煌这样紧紧依偎着歇息,虽然这往往意味着大猫很快就会再吃她一次。
“煌。”按住在自己腹股沟作乱的那只不老实的手,灰喉在黑暗中轻声道:“今天我遇到了……一个感染者。”
“谁?”猫儿的尖牙轻咬着耳翎,舌尖舔着燕子的耳垂。灰喉不耐地摇了摇头,在煌怀里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结果自然是被抱得更紧了。柔顺中不失力道的猫尾环住了腿儿,尾端有一下没一下地撩拨着雪白的大腿内侧。煌的手指也愈发不老实起来。
“听我说。”强压着感觉,灰喉坚定地攥住了煌的手,说起了白天的事。
灵原草场的天空压得很低,云层仿佛就在头顶触手可及的地方懒洋洋地飘浮。在这里,黎博利的视觉可以一下就看到极远方。满目苍绿色的地平尽头是一座黑色的山峦,矫若惊龙般盘虬在草原最北端。灰喉深吸一口气,端稳手中的弩。
“骑射的要领嘛,在于跟着马走;你骑马儿,它颠簸,这是正常的;你别逆着它走,要顺着它,它一颠,你也跟着它的节奏,这样一来,箭就不会颠得没准儿。”
与她并行的是雁骑里的马术教官,一身据说只穿了半年的黛青色军装脏破得有点吓人,边沿都开了线,真不知道是如何打理的。黑黝黝的脸儿上满是伤疤和褶子,偏偏下巴上没胡须,昭示着此人年岁其实不比灰喉大多少的事实。他的马连马鞍都没套,就这么在草原上放马跑走,居然比系鞍而行的灰喉稳当不少。灰喉无暇回应,对着标靶瞄了许久,只感觉浑身上下都在飘,忍不住就要使反劲儿。终于一扣扳机,箭却长了翅膀一般,懒洋洋地钉在标靶一角连十环都够不到的地方。
“已经不错喽。”少年打了个呼哨,灰喉的坐骑像是有灵性一般自己停了下来。燕子有些狼狈地下了马,着地便是一个趔趄,只感觉脚脖子都是酸的。少年好心地伸手过来,他的袖子是撸起来的,灰喉能看到他胳膊上一道道触目心惊的暗青色裂绺,陷在黝黑的皮肤里,内敛着不驯的凶性。但她没犹豫,抓起他的手站起了身。
“你的抑制剂是从哪来的?”休息时间,她问。
“哦,你问这个。”少年活动了一下长着源石的手臂。“都是这里的军爷给的。我们这儿的牧民几乎全都是感染者。”
“全都是?”灰喉惊讶道。少年点点头:“没错儿。本来这灵原老早以前就没有牧民了,有了移动城市,大多数人都进了城当工。那时候谁要是感染了,被巡捕丢进隔离区,那基本命就算没啦。”
“俺爹娘都是牧民,最后进城的那一批。俺从小就跟他们学放马,真不是跟你丫头吹,在这灵原,马术比得上我的,那都还在娘胎里嘞。”一谈到马,少年的眼神里闪着熠熠光辉。灰喉不禁出声提醒:“那么,你又是怎么被感染的呢?是天灾?”
“俺也不清楚。”少年挠挠头。“反正俺记得,当时俺家在城里的工厂旁边,里面的人工河里,都是捅鼻子的水。说不上啥时候就有人被感染,但也说不清,有住在这里的老人说,都怪牧民们离开灵原,‘大黑天’不高兴,要降下惩罚哩。”
“俺被巡捕丢到隔离区,本来以为要没命了。但后来有个军爷,穿得和其他军爷都不一样,进到了隔离区里。听说俺会放马,就带俺走了。俺从此跟他姓了李,行伍里的兄弟都叫俺李鞍儿。”李鞍儿指了指远方地平处牧民搭起的牧包:“现在这里的牧民,大都是城里的感染者,是李大人把大伙救出来,来到这里为军爷们放牧战马。李大人是大伙的大恩人呐!”
“……所以,一切都在变好不是么?就像博士讲的那样,三百年前,人们把感染者活活烧死;二百年前,城市内开始划出隔离区;一百年前,感染者工人开始到工厂里做工。现在,感染者越来越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越来越能融入这个社会了。如果假以时日,是否还会有更明达的改变也未可知——喂,你在听吗?”说到这里,灰喉扭头看了一眼枕边的煌,却看到大猫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闭上。她有些气不打一处来,想要发作,想起煌今天的劳顿却又有些不舍。谁料煌突然睁开眼,露出一个欠揍的笑容:“讲得不错,如果博士听到了你的话,说不准她会怎么夸奖你呢!”
“说正事呢,煌!”气冲冲的燕子想要翻身压上去,结果被大猫借力又翻了一圈——差点一起摔下床——重新压在了身下。大猫在被两人压在被子下的衣服里摸了摸,扯起一截自己衣服上的束带,三下两下就把灰喉的双手妥帖地捆在了身后。
“煌,你做什么——唔!”想要训斥,但随即就被从肩骨慢慢划到尾椎的爱抚给弄得浑身酥软。黎博利的脊背是最脆弱而敏感的位置,中空的脊骨令她们的后背对一切外部的刺激都很敏锐。煌轻轻咬住灰喉的肩头,进攻的方式也从后背蔓延到了身前,手绕过灰喉的身体揉捏着那对椒乳。灰喉急促地喘息着,被约束在身后的双手有意无意地在煌的那对饱满上抓了一把。煌嘻嘻一笑,把胸递到更方便灰喉抓取的位置。
“在床上还敢谈其他人,看来你精力很充沛嘛。”
“我不是那个……唔!”一个灵活的东西突然探入双股之间。一开始还以为是手指,但煌的手还在分别爱抚着自己的胸口与脊背。灰喉用了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那是大猫灵活的尾巴。
煌今晚似乎格外有耐心,尾梢蘸着前次还未干涸的花汁,坏心眼地在灰喉的大腿上一次次涂抹着将尾毛捋顺。灰喉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下意识地去挣扎,但在煌眼中不过是摇晃着身体求爱的信号罢了。
“那里……骗人……”想要抗拒,但是身体被煌从后面牢牢搂住。一次又一次针对脊背的爱抚,几乎能直接靠刺激脊背就能抵达高潮的快感,让灰喉所有的挣扎都变成情欲的碎片。被捆在身后的手臂此时倒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阻碍。煌从后面吻着灰喉的耳翎,又半强迫地让黎博利扭过头来同她接吻。在温暖如潮水覆盖住彼此的时候,灰喉紧绷的身子也渐渐放松了下来。
已经充分润滑的尾梢探入。菲林的尾巴非常灵活,力道也很足,就好像被伸进了一根毛发光滑的触手。明明还没进入多深,灰喉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如同要被顶穿了一样,身体不由自主地弓起。煌连忙来回摩挲她的脊背,感觉少女的喘息比原来更加急促了几分。“怎么了?难受的话马上说出来!”
“蠢……蠢猫……”
“我在,我在呢。”轻轻拍打后背。
“……继续。”
下体的扩张感逐渐被愉悦的感觉抵消,可是空虚感又蔓延上来。灰喉扭动着身体,笨拙地向煌索求。这只蠢猫从来只会蛮打硬拼,但是到了该用力的时候偏偏又停下,等着伴侣沉浸在欲火中而不自知。随着那只猫尾又开始挺近,灰喉轻轻咬住了自己的下唇。对于黎博利狭窄的盆腔来说,这样进入还是有点太猛烈了。但她还是试着接受,蜷缩在身前的双腿抬得更高,主动让煌的尾尖深入到平时所不能到达的地方……
煌不再加以爱抚了,只是静静搂着泪眼婆娑的灰喉,小心地运作着自己的尾巴。尾椎的神经末梢非常细致,连带她此时也已经喘息连连。不经意间升高了的室温笼罩着她们,在进入足够的长度后,尾梢开始缓缓抽回。由于怕毛发断在里面,所以动作比进入时小心了不少,却也撩拨得灰喉更加难以自持。终于随着一声轻响,湿漉漉的猫尾如释重负地在两人之间弹出,带着触电般的轻微抽搐。煌也终于忍不住了,摆正位置将灰喉压在身下。
双人枕上刺绣的鸳鸯倏忽活了过来,随着暧昧的声音展翅高飞,直到良久以后才再度宣告疲倦。
“你啊……还是想的有点太乐观了。”连续两次,就连煌也不由有点微喘。“知道吗?今天下午你练骑射的时候,我可是救了博士一命。”
博士和煌是在刚过午的时候赶到灵原最大的牧民聚居地的。说是聚居地,也不过是一大片简易木栅围起来的牧包帐篷。博士谢绝了李伯明派雁骑护卫的提议,到了最大的牧包门口,她又让煌也原地待命。此时的她依然穿着那身黛青色的军装,这装束无疑赢得了那些感染者牧民的好感。他们热情地把她引到这里最年长的人住的地方。这座牧包是扎眼的白色,顶端扎以银环流苏,无一不显现着其主人的独到身份。
博士小心地跨过门槛,绕过火塘在客位上坐下,身体前倾双手接过主人递来的马奶茶,仅仅几个小小的细节,立刻拉近了她与这里主人的距离。最老的感染者牧民名叫乌斯胡,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了。人虽老了,但也十分健谈。他与博士谈起灵原,总是一口一个军爷如何如何,令博士有些不快。博士问起了灵原北陲的大黑丘,那里有什么说法?
“那大黑丘啊,我们也叫它大黑天,它是神神变化的嘛。”随着老牧民的解释,博士也隐约知道了这黑丘的由来。准确来说,是先有黑丘才有的灵原。据说古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天灾一来便赤地千里。那时有一位身穿黑甲、名叫大黑天的天神与天灾交战,天灾退去后,天神就睡在那里,身躯变成大黑丘。正是大黑丘挡住了千百年来的天灾,灵原草原才得以长久地存在下来。当然,传说不止这一个版本,也有说大黑丘本身是天灾带来的恶神,在山腹里眠着一条条名为大黑天击雷蛟的恶蛟,登上黑丘将被恶蛟缠身,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您认为哪一种传说才是真的?”博士饶有兴致地问。
“这个嘛,大黑天击雷蛟,它是存在的,我是亲眼看见的嘛。”乌斯胡一口干了一碗马奶茶,接着说起自己年轻时的事。当时他偶然经过大黑丘的山脚,亲眼看到无数裹着黑雾的黑蛟在山端翻腾。
“神神变化的地方,它不是人能去的。就算有什么东西守着那儿,它也肯定是有道理嘛。”老人在最后说。两人谈兴正浓,谁也没意识到牧包帘布的一角被悄悄撩开。
“博士!”
一道黑影冲进帐中,扭打声,嘶吼声,一阵痛苦的闷哼。煌把一个半大小子头朝下按在了地上,他剧烈挣扎着,红彤彤的眼睛死盯着穿军装的博士不放,嘴里用不清不楚地喊着。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我在外面看到这家伙鬼鬼祟祟进来,一看就不像个好人。”煌抓住这人的手腕一抖,当的一声,半块尖锐的源石原矿掉在地上,一看就是刻意磨过的锋面比匕首不差多少。虽然被煌制住,这个牧民青年也在不断挣扎“死当官的,还我娘的命,还我娘的命来!”
“出去!”乌斯胡老人倏然站起身,吹胡子瞪眼地喊道:“你个不懂事的娃子,出去!”
“抱歉,抱歉!”外面又进来两个壮硕牧民,不住地对博士道歉,从煌手里几乎是抢过青年拉拽着出了牧包。青年被两个牧民挟持着,仍不忘回头对博士吼:“还我娘的命……我杀了你!杀……”
“快把他带走!关起来!”乌斯胡吼道。转过来面对博士,立刻换上一张笑脸,仿佛刚才的尴尬都没发生过。“抱歉,军爷,这娃子不懂事,不懂……”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母亲怎么了?”博士没有坐下的意思,对煌使了个眼色。乌斯胡犹豫起来:“这……军爷,没事,真的没事,这娃子的母亲是被大户人家看中了,拉去城里做工去了!”
“做工?做什么工?我进来时一路看到,这里男多女少,难道尽皆都要女人做工?”博士愈发追问。乌斯胡老人慌忙摇头:“这……这真不算什么事,军爷!女人都在牧包里做针线活,再说……再说军爷给了我们活路,我们也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您能说明白。”博士皱着眉头,重新坐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证件。“不瞒您说,我是新任的节度参谋。若有什么假公济私、欺霸百姓之事,尽可以如实说了。如果连你们都不肯举,就更不能指望官厅究了不是吗!”
“……大抵是这么回事。不过我又被博士赶出来啦,就没听到后面的内容。但是博士出来的时候,那脸色——”煌做了个鬼脸:“像是谁欠了她钱一样。”
灰喉默不作声,主动往煌的怀里钻了钻。北庭道是大炎边防的中枢,也是边军最大主力所在地之一。这里的水只会比安西道的深。李伯明虽然是博士最信任的学生,但谁知道他有没有藏着什么不见光的秘密?北庭雁骑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感染者牧民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大黑天击雷蛟”又是什么?一个又一个谜题接踵而至,在这个夜晚,相拥的两人同时感觉到如临深渊的不测。
与此同时,博士的营帐彻夜灯火通明。星极走进帐篷,将一封信递给博士。博士阅毕,放进火盆烧掉。
“北庭经略与巡按御史邀伯明一见,伯明请示恩师,是否随同。”
“星极。”棋手小姐沉吟半晌,说:
“明日只你我两人随军进城,我做随侍,你做傅参谋。”
*检校:唐代官制,意为享受该前缀语之后官名的同等地位待遇,不代表实职,中唐以后在地方非常常见。